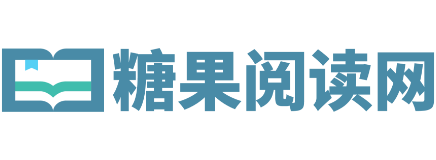辑一 回首见花开 书里书外碎时光
书名: 我从沙漠来 作者:暮千雪 字数:217245
立秋,新秋的霞光清新地拍打着窗户,凭窗望着沐在晨光里的城阙,眼前不觉氤氲起来。昨夜梦里,老屋长院屋檐下的青石台上,父亲曲腿而坐,膝上摊着一本书,《人民文学》还是《收获》?凝神间,那些系在书卷间的记忆,像一只只蝶,拍打着翅迎面飞来……
欢喜与荣耀
初冬的薄暮,几个伙伴在巷子口的老槐树下跳格子,玩得满头大汗时,父亲的大永久滑近眼前。三十出头的父亲,一扬腿利落地下了车子,拍拍口袋,向我招手,确切地说向我们招手。
印象里,小伙伴们见到我父亲都会立马后退几步,有点敬畏又有点爱戴渴盼的目光像星星一样晶亮,因为父亲面对我们时总爱将细长的手指伸进中山装的衣袋,再出来时,手上便多了水果糖或瓜子花生一类。这个戏法每次都逗得贪嘴的孩子吃吃地笑。
这次父亲不例外地又给一帮屁娃带来无穷期待与惊喜,只是大家都推推搡搡得不肯上前,我当然懂得他们的纠结,人穷志不穷,穷人家更是看重自尊,所以家家户户的家长都会叮咛孩子,出门不许吃别人家东西,不要让别人笑话自家寒酸。可是毕竟是孩子,没有几个人能抵制住突然而来的诱惑,况且父亲分明是将该给我的笑容平摊开来,加上他和蔼的话语,我感到几只小手捅在我背上。借着几只小手一推,我便持些许自豪跑到父亲面前,咧着嘴仰起脸,瞅着父亲高高在上的洁净的面孔、笑眯的眼,小辫在后颈窝一晃一晃。父亲呵呵一笑,俯下清瘦的身子,一只手从车把上移到我耳下迅速捏一下,又直起腰身将手伸进中山装口袋,我赶紧将两只手掬过自行车横梁。
父亲掏出的是一大把“鱼皮花生”(花生米上裹一层甜甜的白面,当时的稀罕品),怕滚掉,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地放到我掬着的手心里,我咽口水时听到身后那群小伙伴们压抑的兴奋。父亲又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下,将遗漏的几颗又放到我手心后便推着车往前走,滑了一下车子,上车的腿提了一半又放下,回头叮咛我:尽着人家娃,你吃的机会多。又扬头:分着吃,好好耍,不要打架啊。
嗯,知道,知道啦。父亲的台词孩子们都熟悉,乱喳喳的一堆应答。
父亲满意地一笑,一扬腿跨上车子,向巷子深处骑去。我手捧鱼皮花生不敢乱动,小伙伴们跑上来将我围在了中间,星星般晶亮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我再一次尝到了父亲给我带来的荣光。
看着分到鱼皮花生后的小伙伴一个个左看右看的好奇样,我大咧咧丢一颗进嘴里:这叫鱼皮花生,最好吃啦。鱼皮花生?看一双双毫不掩饰的惊羡眼神,我满足地咯咯地笑催:快吃,快吃。想吃,多的是,以后有了我再给你们吃。
吃了人家的嘴软,伙伴们自觉分占了我的美味,就用好听的来补偿:你爸好很,你爸大方很,要是我爸就不会让我给人家娃吃……
咦呀,你爸车子后边夹的啥?
书呀!
书是干啥的?
书……书是有学问的人看的嘛。
灵光一动呜啦出“学问”一词时,我的自豪感又不可遏制地强烈一分。学问是什么?什么是学问?学问能干啥?这我肯定是一无所知。但看着这些对我惊羡崇拜的流着鼻涕的傻兮兮的面孔,我还是近乎有些傲慢了。估计整个巷子,甚至半条街也只有我爸能认识那密密麻麻的黑字,也只有我爸有条件随身带着那么厚的书,也只有我在我爸我妈的争吵中听过“学问”这个神秘莫测的词。
意犹未尽地吃掉最后一粒,又耍了一会儿,到了鸡上架孩找妈的时候,不知谁说了声我妈在喊我哩,一帮疯够了的屁娃便轰地四下跑散。
“咚”地撞开漆黑木门,跑过悠长的庭院,在二重院落里便看到屋檐下的青石台上曲腿而坐的父亲。借着微弱的霞光,眼睛投在膝上摊开的书页里,手边的青石台上放着一把白色的陶瓷茶壶。
妈!妈!听到我狂呼乱喊,父亲抬头:嘿嘿,土匪!你妈在屋里,还能丢了不成?
我来不及瞅父亲一眼便擦着他肩跳进屋里,母亲条件反射般的大吼:去,洗去,脏死了!
一腔欢喜便被母亲吼得七零八落,噘着嘴去厨房找水。然后又听到母亲在屋里大声指责:看书要紧很?不看书能死人啊?就不知道给娃洗一下,娃是给我一个人生的吗?
哦,父亲恍然,放下手里的书,起身,跨下房台到厨房里给我从缸里取水,再从电壶里倒点热水,两只手指在盆里一划拉,说,行了,不冷不热,刚好。
我边洗脸洗手,不经意地抬头,刚好看到对面的窗户,母亲侧脸贴在玻璃上,原来母亲一直监控着厨房里的一切。
父亲监督我给手上打胰子,胰子滑滑的,我手小,拿不住,一次次掉进水盆里,溅起的水珠子逗得我咯咯地笑。父亲便蹲下来给我打,我还是笑,有些幸灾乐祸的成分,我知道玻璃那边的母亲一定又咬起了牙。
战火连绵
母亲咬牙,肯定是又和父亲吵架了,祸根不用说又是父亲。
父亲有俩“坏习惯”,每天早上刷牙,洗手必用香皂。作为巷子里唯一的国家工人,这些不良癖好,显然脱离了群众。还未从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大方针里走出来的街坊邻里,明里暗里容忍不了父亲这个背叛了自己阶层的资本家恶习,热嘲冷讽不时扑面而来。尤其是在大家一致认为胰子是婆娘娃用的情况下,父亲身上一年四季不断的香皂味成了全巷子婆娘以及男人撇嘴讥笑的资源。
啧啧,瞅,这香味,男人就像个男人的样子么,跟个婆娘一样。
你一年得用几块胰子,要是工厂断货,你可咋活呀?
啧啧,这工人就是不一样,都快赶上城里人啦。
工人,你整天拿胰子搓来搓去,也没见你白嫩到哪里去么,哈哈。
工人,要是停水了,刷不成牙,你是不是就不吃饭?哈哈,难怪这么瘦。
不管是善意的逗乐还是故意的讥笑,父亲依然我行我素。可是山沟出身、经常要和邻里打交道的母亲就撑不住了,她以父亲这些习惯为耻,经常指桑骂槐旁敲侧击的希望父亲知错就改回头是岸,而倔犟的父亲也不示弱。因此,这些也就成了父亲和母亲争吵磨牙的引子,但今天母亲发的邪火,却分明是另有所指。
母亲的这场火起起灭灭地持续了好几天,痛斥的言词里屡屡提及《人民文学》。
你敢把你的《人民文学》拿回来,我就敢给你烧了!你信不信?
嘿嘿,我信,我信,我不拿回来还不行?父亲的认罪态度良好。
《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母亲恨不能将罪魁祸首立马付之于火一样的抡着扫帚将院子扫起一片黄尘。
人民文学是啥?爸。我没长眼色,问了个不该问的话。
是本书,父亲说。
是你爸的祖宗!妈妈吼。
我当然相信我爸,虽然他只是嘿嘿了几声。
显然,父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时光回溯,年青的父亲也的确综合了文学青年的典型元素:清瘦洁净,家族遗传的薄眼皮,细长眼,沉默时显忧郁,笑时明亮纯真。瘦高的身架上长年裹一套藏蓝哔叽呢中山装,冬天时,围条驼色拉毛围脖。
与钟情中山装一样痴情于书的父亲在我们成长里“罪行累累”。据母亲揭发,我们兄妹小时候经常被父亲看书所误,留下了许多不堪的历史。像哥哥玩尿泥,姐姐爬进水盆里等,而我则是不到一岁时,爬到大门口了,看书的父亲还浑然不觉。我爬不回去了,睡着在大门口,被归家的母亲一身泥土地抱回屋,父亲当然被一通好骂。
后来连我都看出个端倪,凡是与书有关的吵架,父亲态度极为驯服,几乎是低声下气了,咋骂都是嘿嘿一笑。母亲有时嗔恼:就知道傻笑?!父亲继续嘿嘿:咱错了嘛,该骂。
错了,就改嘛。母亲趁机教育。
改不了,不由人啊。
母亲颓然:啥不由人?还不是狗改不了吃屎!
母亲与父亲的如此桥段,我们都耳熟能详了,每次只附和着傻笑。
父亲上的是三班倒的班,只要轮班在家,一到黄昏,父亲便端着自己专用的白陶茶壶,腋下夹本或厚或薄或大或小的书,跨出屋子,在屋檐下那块圆青石上一屁股坐下,放下茶壶,躬起双腿,以膝当桌。书一摊开,就如打坐的高僧一样静成一座雕塑。很多次母亲喊他好几声都没反应,最后母亲上去猛地在他肩上一推,他身子一侧大梦初醒地睁着受了惊吓的双眼,那痴痴怔怔地表情逗得母亲忍俊不禁,我们也跟着嘻嘻地乐。当天光完全消散,父亲又会将阵地移到炕上,很多个夜晚,迷迷糊糊一翻身,曚眬睡眼里便是父亲靠着墙看书的画面。昏黄的白炽灯下,沉浸在书香里的父亲年轻的脸容光洁宁静,散发着一种奇妙的光晕,那种光晕让稚气的我踏实地安心地再度入梦。
父亲看书很投入,有时会哈哈大笑,有时会破口大骂,好几次把我吓得哗地爬起来,母亲便催骂父亲:神经病,快睡,娃都让你吓瓜啦。
其实母亲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没有被父亲吓瓜,倒是对父亲手里的书开始充满了好奇,那薄薄的纸里究竟有个什么样的世界,让父亲那样爱不释手?因了这份好奇,我曾多次偷偷地溜进巷口全镇唯一的新华书店,隔着高过头顶的柜台,踮起脚看书架上一排排蒙着厚厚的灰尘的书。那个年轻的女店员不是趴在柜台上睡觉,就是埋头打毛衣,翻飞的指头看得我眼花缭乱。
而父亲带我路过门可罗雀的书店时,总会放慢了脚步,几次都有想进去的意思,原地转两次身后,又继续前行。只是每次都会发出幽叹:书,好东西啊,浪费了真可惜。很多年后想起这一幕时,突然明白当时父亲是不敢进去,他怕进去之后控制不住要买。
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早就捉襟见肘,母亲为了不断柴米油盐,早就殚精竭虑了,连续几年都没有给自己添过新衣服了,而父亲居然擅自订了《人民文学》!待确定父亲的确订了《人民文学》,母亲痛心疾首几近癫狂,又是哭又是骂,她痛恨自己没有及时阻止父亲的坏习惯,怪自己心软对父亲太放纵,骂父亲得寸进尺,从厂里借就罢了,现在发展到不顾婆娘娃死活的地步了……
父母是孩子们的天,接连几天,我们头顶乌云密布,还时不时天雷滚滚,兄妹三人背上都长了眼睛。
后来天雷没有了,但乌云还未散。父亲下班一进门,便是母亲恶狠狠的脸色,尽管父亲一再赔笑脸,尝试跟母亲说话,母亲紧闭着嘴,偶然开次口,也是恫吓:你听着,以后敢拿任何书回来,我都敢给你烧了!烧得一页不留!!你信不信?
信,信,信,嘿嘿。
“痛改前非”的父亲拼命地表现,不停地在家里找活干,扫院子,擦屋子,洗衣洗碗。母亲则在一旁黑着脸“鸡蛋里挑骨头”,这里没扫彻底,那个碗底的油没洗,父亲连忙唯唯诺诺地补救。
当确定家里没有任何活计时,便小心翼翼地向母亲申请:让我看一会书,行不行?就一会会儿。
看啥看?家里书都烧光了!非把你这个毛病治了。母亲纳着鞋底,不抬头地吼。真心说,我是向着父亲的,总觉得母亲在欺负父亲。
嘿嘿……唉……父亲端起茶壶无语地出门,照旧往青石上一坐,手中没有了书,茶壶便托在手间不离。把玩下茶壶,抬头看看天,要么不停地将白陶茶壶高高举过头顶,仰面朝天张开嘴,将茶徐徐倒入口中,发出吸溜吸溜咕叽咕叽的声。我挺喜欢看父亲这个态势,家里没人时,悄悄模仿了一回,结果呛得我连连咳嗽,连带洒湿了衣襟。后来在书上看到李白喝酒的黑白插图,我第一时间想到父亲喝茶的侧影。
有一天下午,又是这般情景,母亲终于不耐烦地发出小声咒骂:抻地跟雁一样,咋不呛死去?
呛死倒享福了,总比这乏味地活着强!这应该是父亲最强烈的牢骚和抗议,只是他是笑呵呵地表达的,我还以为他俩在说笑,同所有见父母和好的娃一样,欢喜地瞅瞅母亲又瞅瞅父亲。但是父亲和母亲又开始玩起沉默,然后母亲起身走开。纳闷间,母亲又折身回来了。
给,给,看,看死去!母亲啪的将几本书砸在父亲身后,父亲惊喜地转身一把抓起:我就知道娃她妈通情达理。原来母亲真的只是将父亲的书藏起来了而已。
甭给我灌迷魂汤了,怕把你急死了,我娃没爸啦。母亲依旧冷着脸,父亲偷偷地笑,我嘻嘻一乐,低头继续趴在椅子上用小木棍算起刚学的进位加法。
惊天逆转
母亲与父亲的这场持久战,更描深了书在我心里的影像,我对书充满了探究欲,尤其记住了《人民文学》。我开始看哥哥拿回来的“娃娃书”,就是黑白连环画,巴掌大,一页一幅图,图下三两行文字。
一看不得了,一下子就沉迷了。短短时间我悄悄买了好多本,8分钱一本的,一毛钱一本的。母亲知道是父亲偷偷给钱买的后破天荒地没有暴跳如雷,只是一看我蹲在一堆书中间看得起劲,就嘟囔:败家子,都是败家子!
幸亏街上及时地出现了摆地摊看书的行当,我就蹲在路边,贪婪地看。二分钱一本,一天花一毛钱我就能看五本。母亲几次把我从书摊前寻回家,我眉飞色舞的样子,母亲的眼波柔了下来。
不知从哪天起,院里人影多了起来。找父亲读家书、代写家书,有冤的找父亲写状子,厂长也亲自派人接父亲回单位替其写发言稿,一时间,父亲成了大家眼中最有文化、最文明、最受尊敬的人。
母亲对父亲的读书及其他恶习也惭愧地接受了,几次在饭桌上说:某某的男人走过去,身上的味把人都能熏死,一天不用胰子不刷牙,某某脏得咋受得了。父亲又是几声嘿嘿,啥也不说。
隔天,窗台上出现了一溜牙缸,个个里面插着崭新的牙刷。母亲也开始刷牙,我家开辟了整条街道全家讲文明的先河。
父亲值夜班不在家,晚上睡不着觉,读过小学三年级的母亲破天荒地翻起了父亲的书。母亲慧心不浅,凭借连读带猜,居然能听到她咯咯的笑声或气愤的咒骂声。
简直是惊天逆转!
某个下午,上完白班的父亲就从厂里搬回一个纸箱子,我们以为是好吃的迫不及待扑过去,结果是多半箱书,清一色尺寸,摞得整整齐齐。兄姐失望地掉头走开了,我倒是满心的惊喜与激动,蹲在纸箱旁看着封面上墨色诱人的《人民文学》四字幸福极了,完全像个穷人突然意外得到一堆金元宝,对未来充满了无忧无虑的安全感,似乎这些书足够我一辈子慢慢享用。端详一会儿后,小心翼翼地抓起一本轻轻摩挲,又假模假样地扮学者将书页翻得哗啦哗啦。
你看看,一本书多少钱?!你爸把多少钱搭在这破书上,那些钱要是给你几个买吃的,要买多少?母亲边拨拉边数落,心疼极了。
嘿嘿,这些比吃啥都有营养。往茶壶里添水的父亲接了话茬。
去,败家子!母亲笑斥,然后提起一本:刚好没啥夹鞋样子,这本我拿了啊。
行行,你想咋就咋,不烧就行。父亲无意中揭了母亲的短。
烧?哼,哪天火了,照样烧。母亲故作板脸。
往后的一年里,懒于写作业的我勤快了,不仅早早将自己语文课本通读认会全书的生字,还把上五年级兄长的语文书也抽空读通,目的是学字。升入五年级时,我开始煞有介事地捧起了《人民文学》。
父亲积攒了几年的《人民文学》成了我流连忘返一沉进去便难以自拔的风景,断绝了和巷子里孩子的玩耍,写完作业便看到入睡。父亲在家时,有不认的字就去问父亲,父亲不在家就自己查字典。
父亲以为我看热闹,有一天抽出一本,翻到一个故事,问我几个问题,我逞能地作了回答。父亲一笑,说,书是好东西,《人民文学》是国家正式刊物,真正的文学,有些道理父母讲不出,凭你们的悟性,自己在书里去寻。
小学毕业,我就开始和父亲抢书看了。尤其到《人民文学》发行的那几天,我格外留意父亲下班的时间。父亲的大永久刚进院子,我便跑过去,追着车子跑,父亲在屋檐下缓缓停下撑车子,我趁机从后架上抽出期待的宝物,怕父亲追讨,转身便往房子跑。父亲便在身后笑着提醒:慢点,土匪!
父亲仍延续着从单位图书馆借书的习惯,《十月》《芙蓉》《开拓》《少年文艺》《故事会》等就是那时候父亲带进我的世界。后来在我的要求下,父亲增大了借读量,在借读的书中出现了《巴黎圣母院》一类的名著,我常常抱着一堆书又笑又跳。暑假,中午知了热得声嘶力竭地鸣叫,我坐在梧桐下的花圃旁沉浸在文字里,脸上、脖子上的汗流啊流,居然丝毫不察。
后来听到心净自然凉一句话时,我相信,世界上是有这种境界的,在那片文字带来的清凉里,我深深地体尝了宁静而丰富的喜悦。
颓败与忧伤
书,带给我欢乐,而迷恋书的父亲一生却是不快乐的,这是初谙人世的我模模糊糊的感知。
书里浸泡久了,父亲难免书呆子气,性情耿直淳厚,对不良现象与虚假伪善之流是深恶痛绝,所以在单位里直言不讳地指出领导不足之后,他一再被排斥。下班回到家里,四邻都是白丁,他只能坐在人堆里嘿嘿憨笑。很多次,书里的故事很精彩,父亲兴高采烈地拉着母亲讲,讲着讲着,母亲就睡着了,父亲就自嘲地嘿嘿一笑。
兄妹三人先后升入初中,而父亲厂里却经常发不出工资濒临倒闭,还要还盖房子的债务……接踵而来的困窘深深地包围着父亲。再加上日益浮躁起来的社会环境和身边一群群生活困苦的四邻,一直有忧国忧民文人情结的父亲更是陷入痛心疾首又爱莫能助的悲哀与无奈中。父亲开始常常发无名的火,我再也不敢和他闹着要书看了,而且,父亲也好久不再看书了。不仅如此,消瘦的颊上开始有皱纹的父亲突然邋遢起来,牙不刷了,澡不洗了,就连身上的衣服都是母亲连催带撵地扒下来洗换。为此,家里时常充斥着谩骂声。
父亲完全被生活打倒了,向现实妥协了,他以颓败的姿态结束了一个书生的清高与斯文。
《人民文学》也理所当然地断订了。
生活拮据,父母亲争吵,少年的敏感令我觉得那是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在家里,我小心翼翼,脚步轻盈,怕一不小心惊扰到眉头紧锁抱膝呆坐的父亲。这都不算什么,最难忍受的是没有新书看。被父亲滋养起来的阅读习惯像毒品一样戒不掉,在书瘾发作难熬之际,我想起了父亲的那个纸箱子。
墙角放了几年的纸箱子很旧很脆,轻轻一扯就裂了几条缝。箱子里的书寥寥无几,是母亲当时在婆娘堆里纳鞋底时抱着夹鞋样的《人民文学》,家里没书的婆娘们立即眼冒亮光地向母亲讨要,母亲便大方地人手一册地送发下去。
残存的十几本《人民文学》像个最忠心的伙伴一样,陪我度过了那段少年的忧伤时期,尽管有时翻着翻着便掉出母亲的鞋样,有时要先取出母亲夹在里边的五彩缤纷的丝线,有时还有姐姐夹的展展的漂亮的糖纸和做毽子的鸡毛。
一天黄昏,我推开院门,抬头的瞬间有欲落泪的冲动。
黯淡的天光里,院子里悄无声息,与大门相对的中间屋里屋门大开,方桌上方60瓦灯泡的昏黄光晕从屋里流泄到檐前。父亲坐在桌旁的方椅上,一条腿垂放在地上,一只脚踩在椅面上,蜷起的膝顶着下颌,贫瘠的腰身,像一把细瘦的弓抵着白色的墙,一动不动的侧脸,眼睛一直愣怔地盯着地面。
孩子般无助凄惶的父亲!十四岁的心倏地涌上莫名的悲凉。父亲,我耿直善良、清高聪敏、洁净谦和的父亲,在生活面前是这样的无能为力手足无措……我轻轻地走进屋里,父亲被惊动,侧过脸来,或许我异样的表情被父亲捕捉到,也被父亲误解了,他牵强地一笑,羞愧地说:过几天,爸再到图书馆给我娃借几本书,等有工资了,爸再给我娃订《人民文学》。
为保护一位父亲的尊严,我没做解释,嗯着点头。
不久,我离开了家。
最大获利者
再回到家时已是十几年后。
三农政策、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浓荫下的新农村、新城镇高楼林立,树绿路阔,让人心情激荡。整洁的庭院,一尘不染的家具,两鬓霜白的父亲依然着身墨蓝中山服,洁净舒展,交递物品间手上有淡淡的力士香皂味,水池上摆着父亲和母亲的牙具,田七牙膏上的笑脸更让人欣慰——政策照顾下,父亲补发了退休金,每个月的退休金足够他和母亲零花,我们兄妹也都成家立业,经常寄钱给他们。
坐在庭院里,欢喜地打量这一切,母亲高兴地住不了嘴:这都是你爸做的,你爸爱干净是出了名的。父亲在一旁像个小孩子一样有点羞涩,他是不是忆起了自己生命中一段落魄的日子?
爸,你看。我拿出有自己文字的报纸给父亲看。
我娃写的?父亲对着报纸上我的名字细眯的眼倏地一亮,惊喜地放下了手中的茶壶。父亲年轻时喝茶就不用杯子,老了更是一把茶壶不离手。
对啊。我故作得意。
你啥时会写文章的?谁教你的?父亲连连追问。
你教的,从小就跟你学呀。
我教的?父亲困惑地眯直细长的眼。
您忘了您的百宝箱?《人民文学》!
你真的是受那个影响?父亲很惊喜。
对,我到现在还记得一篇小说的最后一句是:看着远处的桥,他有些明白,人生就是座连绵起伏的拱桥,有上坡的阶段,也有下坡的阶段。这句话,帮了我很多次。
看看,鼠目寸光地骂我看书是不务正业,骂我订《人民文学》是最大的浪费,现在你还有啥话说?父亲笑着追讨母亲。
你现在订,我保证支持,一个月订十本我都不骂了。母亲笑语。
嘿嘿,你知道我现在退休了,没地方订了。
让娃给你买嘛。母亲建议。
父亲眼一亮,又像探听老朋友音讯一样认真地问我:对了,娃,现在《人民文学》还有没有?
有,变得更精美了,不过内容还是很过硬,依然是主流文学的引导者。
嘿嘿,那就好。父亲明显地放心舒了一口气,估计一直怀有忧国忧民的文人情结的父亲是担心在商文结合的当下,《人民文学》是不是也失去了最初的导向。
爸,下次回来,我给你买几本,《芙蓉》《十月》我也给你买上。
行呀,嘿,记得了就带,忘了也不咋,我眼睛不行了,看书都是做样子哩。我知道父亲是怕给我添麻烦。
绝对忘不了,我可是你俩一辈子战争中的最大获利者啊!
嘿嘿,嘿嘿。父亲母亲相视一笑,父亲从记忆里的低眉顺眼变成得意,母亲笑得有一丝羞愧。
可是,后来几次回家,居然给忘了!!接到父亲猝然离世的消息,我眼前第一刻跳出的是父亲望门长盼的神情,泪水奔涌里想起坐在屋檐下青石台雕塑一样读书的父亲,想起昏黄的白炽灯下靠在炕头执着看书的父亲,想起给母亲讲书、发现母亲已入睡后自嘲地悠叹的父亲……
我忽然懂了父亲一生埋藏在书页里的孤独。漫长的人生里,父亲或许只有在捧起书时,才会从深凉的孤独中泅渡出来,享受到一丝生命的欢欣,而《人民文学》是父亲为孱弱的生命点亮的一盏希望之灯,而我在父亲的灯下也找到了方向……
父亲下葬了,在父亲墓穴里亮着烛灯的小桌上是两本摊开的书,因为当时镇上找不到《人民文学》,只好用别的书替代。我想慈蔼的父亲一定不会怪我的吧,而有书相陪,在天国里,他一定不再孤独……
欢喜与荣耀
初冬的薄暮,几个伙伴在巷子口的老槐树下跳格子,玩得满头大汗时,父亲的大永久滑近眼前。三十出头的父亲,一扬腿利落地下了车子,拍拍口袋,向我招手,确切地说向我们招手。
印象里,小伙伴们见到我父亲都会立马后退几步,有点敬畏又有点爱戴渴盼的目光像星星一样晶亮,因为父亲面对我们时总爱将细长的手指伸进中山装的衣袋,再出来时,手上便多了水果糖或瓜子花生一类。这个戏法每次都逗得贪嘴的孩子吃吃地笑。
这次父亲不例外地又给一帮屁娃带来无穷期待与惊喜,只是大家都推推搡搡得不肯上前,我当然懂得他们的纠结,人穷志不穷,穷人家更是看重自尊,所以家家户户的家长都会叮咛孩子,出门不许吃别人家东西,不要让别人笑话自家寒酸。可是毕竟是孩子,没有几个人能抵制住突然而来的诱惑,况且父亲分明是将该给我的笑容平摊开来,加上他和蔼的话语,我感到几只小手捅在我背上。借着几只小手一推,我便持些许自豪跑到父亲面前,咧着嘴仰起脸,瞅着父亲高高在上的洁净的面孔、笑眯的眼,小辫在后颈窝一晃一晃。父亲呵呵一笑,俯下清瘦的身子,一只手从车把上移到我耳下迅速捏一下,又直起腰身将手伸进中山装口袋,我赶紧将两只手掬过自行车横梁。
父亲掏出的是一大把“鱼皮花生”(花生米上裹一层甜甜的白面,当时的稀罕品),怕滚掉,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地放到我掬着的手心里,我咽口水时听到身后那群小伙伴们压抑的兴奋。父亲又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下,将遗漏的几颗又放到我手心后便推着车往前走,滑了一下车子,上车的腿提了一半又放下,回头叮咛我:尽着人家娃,你吃的机会多。又扬头:分着吃,好好耍,不要打架啊。
嗯,知道,知道啦。父亲的台词孩子们都熟悉,乱喳喳的一堆应答。
父亲满意地一笑,一扬腿跨上车子,向巷子深处骑去。我手捧鱼皮花生不敢乱动,小伙伴们跑上来将我围在了中间,星星般晶亮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我再一次尝到了父亲给我带来的荣光。
看着分到鱼皮花生后的小伙伴一个个左看右看的好奇样,我大咧咧丢一颗进嘴里:这叫鱼皮花生,最好吃啦。鱼皮花生?看一双双毫不掩饰的惊羡眼神,我满足地咯咯地笑催:快吃,快吃。想吃,多的是,以后有了我再给你们吃。
吃了人家的嘴软,伙伴们自觉分占了我的美味,就用好听的来补偿:你爸好很,你爸大方很,要是我爸就不会让我给人家娃吃……
咦呀,你爸车子后边夹的啥?
书呀!
书是干啥的?
书……书是有学问的人看的嘛。
灵光一动呜啦出“学问”一词时,我的自豪感又不可遏制地强烈一分。学问是什么?什么是学问?学问能干啥?这我肯定是一无所知。但看着这些对我惊羡崇拜的流着鼻涕的傻兮兮的面孔,我还是近乎有些傲慢了。估计整个巷子,甚至半条街也只有我爸能认识那密密麻麻的黑字,也只有我爸有条件随身带着那么厚的书,也只有我在我爸我妈的争吵中听过“学问”这个神秘莫测的词。
意犹未尽地吃掉最后一粒,又耍了一会儿,到了鸡上架孩找妈的时候,不知谁说了声我妈在喊我哩,一帮疯够了的屁娃便轰地四下跑散。
“咚”地撞开漆黑木门,跑过悠长的庭院,在二重院落里便看到屋檐下的青石台上曲腿而坐的父亲。借着微弱的霞光,眼睛投在膝上摊开的书页里,手边的青石台上放着一把白色的陶瓷茶壶。
妈!妈!听到我狂呼乱喊,父亲抬头:嘿嘿,土匪!你妈在屋里,还能丢了不成?
我来不及瞅父亲一眼便擦着他肩跳进屋里,母亲条件反射般的大吼:去,洗去,脏死了!
一腔欢喜便被母亲吼得七零八落,噘着嘴去厨房找水。然后又听到母亲在屋里大声指责:看书要紧很?不看书能死人啊?就不知道给娃洗一下,娃是给我一个人生的吗?
哦,父亲恍然,放下手里的书,起身,跨下房台到厨房里给我从缸里取水,再从电壶里倒点热水,两只手指在盆里一划拉,说,行了,不冷不热,刚好。
我边洗脸洗手,不经意地抬头,刚好看到对面的窗户,母亲侧脸贴在玻璃上,原来母亲一直监控着厨房里的一切。
父亲监督我给手上打胰子,胰子滑滑的,我手小,拿不住,一次次掉进水盆里,溅起的水珠子逗得我咯咯地笑。父亲便蹲下来给我打,我还是笑,有些幸灾乐祸的成分,我知道玻璃那边的母亲一定又咬起了牙。
战火连绵
母亲咬牙,肯定是又和父亲吵架了,祸根不用说又是父亲。
父亲有俩“坏习惯”,每天早上刷牙,洗手必用香皂。作为巷子里唯一的国家工人,这些不良癖好,显然脱离了群众。还未从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大方针里走出来的街坊邻里,明里暗里容忍不了父亲这个背叛了自己阶层的资本家恶习,热嘲冷讽不时扑面而来。尤其是在大家一致认为胰子是婆娘娃用的情况下,父亲身上一年四季不断的香皂味成了全巷子婆娘以及男人撇嘴讥笑的资源。
啧啧,瞅,这香味,男人就像个男人的样子么,跟个婆娘一样。
你一年得用几块胰子,要是工厂断货,你可咋活呀?
啧啧,这工人就是不一样,都快赶上城里人啦。
工人,你整天拿胰子搓来搓去,也没见你白嫩到哪里去么,哈哈。
工人,要是停水了,刷不成牙,你是不是就不吃饭?哈哈,难怪这么瘦。
不管是善意的逗乐还是故意的讥笑,父亲依然我行我素。可是山沟出身、经常要和邻里打交道的母亲就撑不住了,她以父亲这些习惯为耻,经常指桑骂槐旁敲侧击的希望父亲知错就改回头是岸,而倔犟的父亲也不示弱。因此,这些也就成了父亲和母亲争吵磨牙的引子,但今天母亲发的邪火,却分明是另有所指。
母亲的这场火起起灭灭地持续了好几天,痛斥的言词里屡屡提及《人民文学》。
你敢把你的《人民文学》拿回来,我就敢给你烧了!你信不信?
嘿嘿,我信,我信,我不拿回来还不行?父亲的认罪态度良好。
《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母亲恨不能将罪魁祸首立马付之于火一样的抡着扫帚将院子扫起一片黄尘。
人民文学是啥?爸。我没长眼色,问了个不该问的话。
是本书,父亲说。
是你爸的祖宗!妈妈吼。
我当然相信我爸,虽然他只是嘿嘿了几声。
显然,父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时光回溯,年青的父亲也的确综合了文学青年的典型元素:清瘦洁净,家族遗传的薄眼皮,细长眼,沉默时显忧郁,笑时明亮纯真。瘦高的身架上长年裹一套藏蓝哔叽呢中山装,冬天时,围条驼色拉毛围脖。
与钟情中山装一样痴情于书的父亲在我们成长里“罪行累累”。据母亲揭发,我们兄妹小时候经常被父亲看书所误,留下了许多不堪的历史。像哥哥玩尿泥,姐姐爬进水盆里等,而我则是不到一岁时,爬到大门口了,看书的父亲还浑然不觉。我爬不回去了,睡着在大门口,被归家的母亲一身泥土地抱回屋,父亲当然被一通好骂。
后来连我都看出个端倪,凡是与书有关的吵架,父亲态度极为驯服,几乎是低声下气了,咋骂都是嘿嘿一笑。母亲有时嗔恼:就知道傻笑?!父亲继续嘿嘿:咱错了嘛,该骂。
错了,就改嘛。母亲趁机教育。
改不了,不由人啊。
母亲颓然:啥不由人?还不是狗改不了吃屎!
母亲与父亲的如此桥段,我们都耳熟能详了,每次只附和着傻笑。
父亲上的是三班倒的班,只要轮班在家,一到黄昏,父亲便端着自己专用的白陶茶壶,腋下夹本或厚或薄或大或小的书,跨出屋子,在屋檐下那块圆青石上一屁股坐下,放下茶壶,躬起双腿,以膝当桌。书一摊开,就如打坐的高僧一样静成一座雕塑。很多次母亲喊他好几声都没反应,最后母亲上去猛地在他肩上一推,他身子一侧大梦初醒地睁着受了惊吓的双眼,那痴痴怔怔地表情逗得母亲忍俊不禁,我们也跟着嘻嘻地乐。当天光完全消散,父亲又会将阵地移到炕上,很多个夜晚,迷迷糊糊一翻身,曚眬睡眼里便是父亲靠着墙看书的画面。昏黄的白炽灯下,沉浸在书香里的父亲年轻的脸容光洁宁静,散发着一种奇妙的光晕,那种光晕让稚气的我踏实地安心地再度入梦。
父亲看书很投入,有时会哈哈大笑,有时会破口大骂,好几次把我吓得哗地爬起来,母亲便催骂父亲:神经病,快睡,娃都让你吓瓜啦。
其实母亲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没有被父亲吓瓜,倒是对父亲手里的书开始充满了好奇,那薄薄的纸里究竟有个什么样的世界,让父亲那样爱不释手?因了这份好奇,我曾多次偷偷地溜进巷口全镇唯一的新华书店,隔着高过头顶的柜台,踮起脚看书架上一排排蒙着厚厚的灰尘的书。那个年轻的女店员不是趴在柜台上睡觉,就是埋头打毛衣,翻飞的指头看得我眼花缭乱。
而父亲带我路过门可罗雀的书店时,总会放慢了脚步,几次都有想进去的意思,原地转两次身后,又继续前行。只是每次都会发出幽叹:书,好东西啊,浪费了真可惜。很多年后想起这一幕时,突然明白当时父亲是不敢进去,他怕进去之后控制不住要买。
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早就捉襟见肘,母亲为了不断柴米油盐,早就殚精竭虑了,连续几年都没有给自己添过新衣服了,而父亲居然擅自订了《人民文学》!待确定父亲的确订了《人民文学》,母亲痛心疾首几近癫狂,又是哭又是骂,她痛恨自己没有及时阻止父亲的坏习惯,怪自己心软对父亲太放纵,骂父亲得寸进尺,从厂里借就罢了,现在发展到不顾婆娘娃死活的地步了……
父母是孩子们的天,接连几天,我们头顶乌云密布,还时不时天雷滚滚,兄妹三人背上都长了眼睛。
后来天雷没有了,但乌云还未散。父亲下班一进门,便是母亲恶狠狠的脸色,尽管父亲一再赔笑脸,尝试跟母亲说话,母亲紧闭着嘴,偶然开次口,也是恫吓:你听着,以后敢拿任何书回来,我都敢给你烧了!烧得一页不留!!你信不信?
信,信,信,嘿嘿。
“痛改前非”的父亲拼命地表现,不停地在家里找活干,扫院子,擦屋子,洗衣洗碗。母亲则在一旁黑着脸“鸡蛋里挑骨头”,这里没扫彻底,那个碗底的油没洗,父亲连忙唯唯诺诺地补救。
当确定家里没有任何活计时,便小心翼翼地向母亲申请:让我看一会书,行不行?就一会会儿。
看啥看?家里书都烧光了!非把你这个毛病治了。母亲纳着鞋底,不抬头地吼。真心说,我是向着父亲的,总觉得母亲在欺负父亲。
嘿嘿……唉……父亲端起茶壶无语地出门,照旧往青石上一坐,手中没有了书,茶壶便托在手间不离。把玩下茶壶,抬头看看天,要么不停地将白陶茶壶高高举过头顶,仰面朝天张开嘴,将茶徐徐倒入口中,发出吸溜吸溜咕叽咕叽的声。我挺喜欢看父亲这个态势,家里没人时,悄悄模仿了一回,结果呛得我连连咳嗽,连带洒湿了衣襟。后来在书上看到李白喝酒的黑白插图,我第一时间想到父亲喝茶的侧影。
有一天下午,又是这般情景,母亲终于不耐烦地发出小声咒骂:抻地跟雁一样,咋不呛死去?
呛死倒享福了,总比这乏味地活着强!这应该是父亲最强烈的牢骚和抗议,只是他是笑呵呵地表达的,我还以为他俩在说笑,同所有见父母和好的娃一样,欢喜地瞅瞅母亲又瞅瞅父亲。但是父亲和母亲又开始玩起沉默,然后母亲起身走开。纳闷间,母亲又折身回来了。
给,给,看,看死去!母亲啪的将几本书砸在父亲身后,父亲惊喜地转身一把抓起:我就知道娃她妈通情达理。原来母亲真的只是将父亲的书藏起来了而已。
甭给我灌迷魂汤了,怕把你急死了,我娃没爸啦。母亲依旧冷着脸,父亲偷偷地笑,我嘻嘻一乐,低头继续趴在椅子上用小木棍算起刚学的进位加法。
惊天逆转
母亲与父亲的这场持久战,更描深了书在我心里的影像,我对书充满了探究欲,尤其记住了《人民文学》。我开始看哥哥拿回来的“娃娃书”,就是黑白连环画,巴掌大,一页一幅图,图下三两行文字。
一看不得了,一下子就沉迷了。短短时间我悄悄买了好多本,8分钱一本的,一毛钱一本的。母亲知道是父亲偷偷给钱买的后破天荒地没有暴跳如雷,只是一看我蹲在一堆书中间看得起劲,就嘟囔:败家子,都是败家子!
幸亏街上及时地出现了摆地摊看书的行当,我就蹲在路边,贪婪地看。二分钱一本,一天花一毛钱我就能看五本。母亲几次把我从书摊前寻回家,我眉飞色舞的样子,母亲的眼波柔了下来。
不知从哪天起,院里人影多了起来。找父亲读家书、代写家书,有冤的找父亲写状子,厂长也亲自派人接父亲回单位替其写发言稿,一时间,父亲成了大家眼中最有文化、最文明、最受尊敬的人。
母亲对父亲的读书及其他恶习也惭愧地接受了,几次在饭桌上说:某某的男人走过去,身上的味把人都能熏死,一天不用胰子不刷牙,某某脏得咋受得了。父亲又是几声嘿嘿,啥也不说。
隔天,窗台上出现了一溜牙缸,个个里面插着崭新的牙刷。母亲也开始刷牙,我家开辟了整条街道全家讲文明的先河。
父亲值夜班不在家,晚上睡不着觉,读过小学三年级的母亲破天荒地翻起了父亲的书。母亲慧心不浅,凭借连读带猜,居然能听到她咯咯的笑声或气愤的咒骂声。
简直是惊天逆转!
某个下午,上完白班的父亲就从厂里搬回一个纸箱子,我们以为是好吃的迫不及待扑过去,结果是多半箱书,清一色尺寸,摞得整整齐齐。兄姐失望地掉头走开了,我倒是满心的惊喜与激动,蹲在纸箱旁看着封面上墨色诱人的《人民文学》四字幸福极了,完全像个穷人突然意外得到一堆金元宝,对未来充满了无忧无虑的安全感,似乎这些书足够我一辈子慢慢享用。端详一会儿后,小心翼翼地抓起一本轻轻摩挲,又假模假样地扮学者将书页翻得哗啦哗啦。
你看看,一本书多少钱?!你爸把多少钱搭在这破书上,那些钱要是给你几个买吃的,要买多少?母亲边拨拉边数落,心疼极了。
嘿嘿,这些比吃啥都有营养。往茶壶里添水的父亲接了话茬。
去,败家子!母亲笑斥,然后提起一本:刚好没啥夹鞋样子,这本我拿了啊。
行行,你想咋就咋,不烧就行。父亲无意中揭了母亲的短。
烧?哼,哪天火了,照样烧。母亲故作板脸。
往后的一年里,懒于写作业的我勤快了,不仅早早将自己语文课本通读认会全书的生字,还把上五年级兄长的语文书也抽空读通,目的是学字。升入五年级时,我开始煞有介事地捧起了《人民文学》。
父亲积攒了几年的《人民文学》成了我流连忘返一沉进去便难以自拔的风景,断绝了和巷子里孩子的玩耍,写完作业便看到入睡。父亲在家时,有不认的字就去问父亲,父亲不在家就自己查字典。
父亲以为我看热闹,有一天抽出一本,翻到一个故事,问我几个问题,我逞能地作了回答。父亲一笑,说,书是好东西,《人民文学》是国家正式刊物,真正的文学,有些道理父母讲不出,凭你们的悟性,自己在书里去寻。
小学毕业,我就开始和父亲抢书看了。尤其到《人民文学》发行的那几天,我格外留意父亲下班的时间。父亲的大永久刚进院子,我便跑过去,追着车子跑,父亲在屋檐下缓缓停下撑车子,我趁机从后架上抽出期待的宝物,怕父亲追讨,转身便往房子跑。父亲便在身后笑着提醒:慢点,土匪!
父亲仍延续着从单位图书馆借书的习惯,《十月》《芙蓉》《开拓》《少年文艺》《故事会》等就是那时候父亲带进我的世界。后来在我的要求下,父亲增大了借读量,在借读的书中出现了《巴黎圣母院》一类的名著,我常常抱着一堆书又笑又跳。暑假,中午知了热得声嘶力竭地鸣叫,我坐在梧桐下的花圃旁沉浸在文字里,脸上、脖子上的汗流啊流,居然丝毫不察。
后来听到心净自然凉一句话时,我相信,世界上是有这种境界的,在那片文字带来的清凉里,我深深地体尝了宁静而丰富的喜悦。
颓败与忧伤
书,带给我欢乐,而迷恋书的父亲一生却是不快乐的,这是初谙人世的我模模糊糊的感知。
书里浸泡久了,父亲难免书呆子气,性情耿直淳厚,对不良现象与虚假伪善之流是深恶痛绝,所以在单位里直言不讳地指出领导不足之后,他一再被排斥。下班回到家里,四邻都是白丁,他只能坐在人堆里嘿嘿憨笑。很多次,书里的故事很精彩,父亲兴高采烈地拉着母亲讲,讲着讲着,母亲就睡着了,父亲就自嘲地嘿嘿一笑。
兄妹三人先后升入初中,而父亲厂里却经常发不出工资濒临倒闭,还要还盖房子的债务……接踵而来的困窘深深地包围着父亲。再加上日益浮躁起来的社会环境和身边一群群生活困苦的四邻,一直有忧国忧民文人情结的父亲更是陷入痛心疾首又爱莫能助的悲哀与无奈中。父亲开始常常发无名的火,我再也不敢和他闹着要书看了,而且,父亲也好久不再看书了。不仅如此,消瘦的颊上开始有皱纹的父亲突然邋遢起来,牙不刷了,澡不洗了,就连身上的衣服都是母亲连催带撵地扒下来洗换。为此,家里时常充斥着谩骂声。
父亲完全被生活打倒了,向现实妥协了,他以颓败的姿态结束了一个书生的清高与斯文。
《人民文学》也理所当然地断订了。
生活拮据,父母亲争吵,少年的敏感令我觉得那是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在家里,我小心翼翼,脚步轻盈,怕一不小心惊扰到眉头紧锁抱膝呆坐的父亲。这都不算什么,最难忍受的是没有新书看。被父亲滋养起来的阅读习惯像毒品一样戒不掉,在书瘾发作难熬之际,我想起了父亲的那个纸箱子。
墙角放了几年的纸箱子很旧很脆,轻轻一扯就裂了几条缝。箱子里的书寥寥无几,是母亲当时在婆娘堆里纳鞋底时抱着夹鞋样的《人民文学》,家里没书的婆娘们立即眼冒亮光地向母亲讨要,母亲便大方地人手一册地送发下去。
残存的十几本《人民文学》像个最忠心的伙伴一样,陪我度过了那段少年的忧伤时期,尽管有时翻着翻着便掉出母亲的鞋样,有时要先取出母亲夹在里边的五彩缤纷的丝线,有时还有姐姐夹的展展的漂亮的糖纸和做毽子的鸡毛。
一天黄昏,我推开院门,抬头的瞬间有欲落泪的冲动。
黯淡的天光里,院子里悄无声息,与大门相对的中间屋里屋门大开,方桌上方60瓦灯泡的昏黄光晕从屋里流泄到檐前。父亲坐在桌旁的方椅上,一条腿垂放在地上,一只脚踩在椅面上,蜷起的膝顶着下颌,贫瘠的腰身,像一把细瘦的弓抵着白色的墙,一动不动的侧脸,眼睛一直愣怔地盯着地面。
孩子般无助凄惶的父亲!十四岁的心倏地涌上莫名的悲凉。父亲,我耿直善良、清高聪敏、洁净谦和的父亲,在生活面前是这样的无能为力手足无措……我轻轻地走进屋里,父亲被惊动,侧过脸来,或许我异样的表情被父亲捕捉到,也被父亲误解了,他牵强地一笑,羞愧地说:过几天,爸再到图书馆给我娃借几本书,等有工资了,爸再给我娃订《人民文学》。
为保护一位父亲的尊严,我没做解释,嗯着点头。
不久,我离开了家。
最大获利者
再回到家时已是十几年后。
三农政策、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浓荫下的新农村、新城镇高楼林立,树绿路阔,让人心情激荡。整洁的庭院,一尘不染的家具,两鬓霜白的父亲依然着身墨蓝中山服,洁净舒展,交递物品间手上有淡淡的力士香皂味,水池上摆着父亲和母亲的牙具,田七牙膏上的笑脸更让人欣慰——政策照顾下,父亲补发了退休金,每个月的退休金足够他和母亲零花,我们兄妹也都成家立业,经常寄钱给他们。
坐在庭院里,欢喜地打量这一切,母亲高兴地住不了嘴:这都是你爸做的,你爸爱干净是出了名的。父亲在一旁像个小孩子一样有点羞涩,他是不是忆起了自己生命中一段落魄的日子?
爸,你看。我拿出有自己文字的报纸给父亲看。
我娃写的?父亲对着报纸上我的名字细眯的眼倏地一亮,惊喜地放下了手中的茶壶。父亲年轻时喝茶就不用杯子,老了更是一把茶壶不离手。
对啊。我故作得意。
你啥时会写文章的?谁教你的?父亲连连追问。
你教的,从小就跟你学呀。
我教的?父亲困惑地眯直细长的眼。
您忘了您的百宝箱?《人民文学》!
你真的是受那个影响?父亲很惊喜。
对,我到现在还记得一篇小说的最后一句是:看着远处的桥,他有些明白,人生就是座连绵起伏的拱桥,有上坡的阶段,也有下坡的阶段。这句话,帮了我很多次。
看看,鼠目寸光地骂我看书是不务正业,骂我订《人民文学》是最大的浪费,现在你还有啥话说?父亲笑着追讨母亲。
你现在订,我保证支持,一个月订十本我都不骂了。母亲笑语。
嘿嘿,你知道我现在退休了,没地方订了。
让娃给你买嘛。母亲建议。
父亲眼一亮,又像探听老朋友音讯一样认真地问我:对了,娃,现在《人民文学》还有没有?
有,变得更精美了,不过内容还是很过硬,依然是主流文学的引导者。
嘿嘿,那就好。父亲明显地放心舒了一口气,估计一直怀有忧国忧民的文人情结的父亲是担心在商文结合的当下,《人民文学》是不是也失去了最初的导向。
爸,下次回来,我给你买几本,《芙蓉》《十月》我也给你买上。
行呀,嘿,记得了就带,忘了也不咋,我眼睛不行了,看书都是做样子哩。我知道父亲是怕给我添麻烦。
绝对忘不了,我可是你俩一辈子战争中的最大获利者啊!
嘿嘿,嘿嘿。父亲母亲相视一笑,父亲从记忆里的低眉顺眼变成得意,母亲笑得有一丝羞愧。
可是,后来几次回家,居然给忘了!!接到父亲猝然离世的消息,我眼前第一刻跳出的是父亲望门长盼的神情,泪水奔涌里想起坐在屋檐下青石台雕塑一样读书的父亲,想起昏黄的白炽灯下靠在炕头执着看书的父亲,想起给母亲讲书、发现母亲已入睡后自嘲地悠叹的父亲……
我忽然懂了父亲一生埋藏在书页里的孤独。漫长的人生里,父亲或许只有在捧起书时,才会从深凉的孤独中泅渡出来,享受到一丝生命的欢欣,而《人民文学》是父亲为孱弱的生命点亮的一盏希望之灯,而我在父亲的灯下也找到了方向……
父亲下葬了,在父亲墓穴里亮着烛灯的小桌上是两本摊开的书,因为当时镇上找不到《人民文学》,只好用别的书替代。我想慈蔼的父亲一定不会怪我的吧,而有书相陪,在天国里,他一定不再孤独……